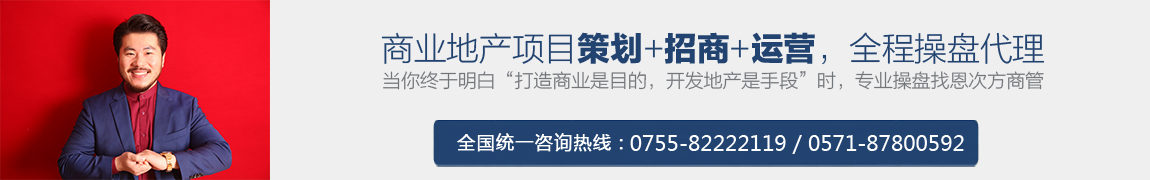
然而,包括闵行卫星城在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卫星城规划建设过于强调主业发展,忽视主辅产业的多元化协调发展;加之,由于种种因素造成规划建设出现断层,导致卫星城发展停滞,难以发挥产业密集的优势,人口聚集的“反磁力”效应也大打折扣。这些得失在当代上海郊区新城规划建设过程中值得借鉴和警示。
闵行卫星城规划建设的成功之道
闵行卫星城位于申城西南部,黄浦江上游北岸,距市中心约32公里,是上海最早规划并实施建设的两个卫星城之一(另一个是吴泾)。1958-1959年,闵行卫星城共新建工业建筑21.1万平方米,住宅18万平方米,铁路36.9公里,公路50公里,发电厂和自来水厂各一座,建设成就斐然。
总体而言,闵行卫星城规划建设的成功之道大致有以下三点:
首先,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了闵行地区的原有基础,并适度控制发展规模。一般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卫星城有两种建设开发模式,即传统与现代结合型和纯现代工业化型。闵行卫星城属于前者。
传统元素方面,闵行卫星城的主体区域是闵行镇。闵行镇为上海县的经济文化中心,素有“小上海”之称,在解放前后曾两度作为县治所在地。解放之初,闵行镇各业店铺行号达300家,占上海县商户总数的18.4%。工业方面,1933年,董荣清等在闵行镇创建了上海第一家民族化工染料生产企业-中孚染料厂。1946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通用机器有限公司在当地设立制造厂。闵行卫星城的发展有其先天的历史底蕴和根基。
解放后,闵行镇区域的工业生产更是有了长足发展。早在1950年代初,原设于闵行镇的华东工业部上海通用机器厂(1953年更名为上海汽轮机厂)、中孚化工厂先后扩建;上海电机厂也从市区迁至闵行建造新厂。1953年,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闵行建成上海市电站设备生产基地。1954年在华东工业部主持下,闵行镇市政规划委员会确定将闵行建设成为一个以机械工业生产为主的小型城市,规划人口规模6万人,用地513公顷,工业布局主要沿黄浦江北岸沙港至竹港间。至1957年闵行地区已拥有人口3.7万人,其中职工约8300人,云集了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中联染料厂(即由中孚化工厂等合并而成)、达丰化工厂等大中型企业。当地交通运输条件良好,5000吨左右的船只可从吴淞口直达闵行;由沪闵路直达市中心区,经北松(北桥至松江)、北吴(北桥至吴泾)公路分别通往松江和吴泾;供电、供水及公共服务设施都有一定的基础。因此,以机电工业为主的闵行卫星城在起步之初就已有相当雄厚的产业基础。
在上海市城市建设局规划设计院1959年11月制定的《近郊工业区及卫星城镇1960年建厂计划及地区建设条件》中,将闵行卫星城的人口总数定为20万-25万,总用地23平方公里,其中生产性用地7平方公里。文件还确定了闵行卫星城的规划原则:控制城镇发展规模,除现已确定建设的工业外,原则上不再增设新的大型企业及与现有企业无协作关系的企业。
其次,城市建设与农村建设有机融合。闵行卫星城在规划建设期间,向毗邻的马桥公社征地约1.2万亩,涉及农户572户。为了妥善解决这些征地农民的生活问题,建设方事前充分考虑到了农民安置点的规划建设,在利用旧镇拆迁的物料和工业企业提供的拆迁补偿费的基础上,配比一定的物力财力,在卫星城北部兴建了马桥公社居民点,并协助公社开办了两家集体工厂,吸收征地农民务工劳动。这一系列举措当地农民很满意,卫星城工业用地问题也迎刃而解,仅用两三周时间就完成了征地工作,实现了工农两利。
第三,本着“就地生产,就地生活”的原则,着力加大配置生活配套设施。闵行地区在1953年就建成了近10万平方米的电机新村工人住宅区,1957年约10万平方米的汽轮新村竣工。在此基础上,闵行卫星城根据规划又大规模兴建住宅。其中,“闵行一条街”成为上海卫星城建设、乃至新中国工业新城规划建设的样板。
1959年3月上海市建设委员会确定“闵行一号路成街成坊建筑”的规划方案。1959年4月3日,第一期工程破土动工,于建国10周年国庆前夕完竣。一期工程不仅耗时短,而且建筑外形美观、色彩各异,富于浓郁的民族风格。沿街商业业态和商品品种也比较丰富,基本能够满足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闵行一条街”被当时的新闻媒体赞誉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街”。
1959年10月,第二期工程紧接着展开,在今江川路南北、兰坪路东西两侧建成住宅、商业配套设施共约8.4万平方米,形成东风一村和东风二村。1960年起,沿街建筑向西延伸,在今江川路南北、瑞丽路东西两侧又兴建了大量住宅和公建配套建筑。这些规模化的住宅建筑和公共设施大幅度提高了闵行卫星城的适居度,为推动卫星城的工业化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闵行卫星城规划建设的美中不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大规模的卫星城建设是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闵行卫星城规划建设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冒进思想的影响。加之,闵行卫星城建设是卫星城规划理论首次在上海付诸实践,实施过程中出现瑕疵在所难免。1959年,上海市规划设计院对1958年闵行卫星城规划在人口规模、用地性质和绿化等方面作局部修改。但这种微调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消弭规划本身的时代缺陷。
当然,闵行卫星城在规划建设方面的“先天不足”并非在建设之初就暴露出来。恰恰相反,闵行卫星城建设初期的高速发展正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先天不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重生产、轻生活”的建设指导思想所导致的工业化目标与城市现代化目标的错位,使闵行卫星城原先隐藏的问题不断发酵,并滋生出新的矛盾,以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渐显露出来。
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不足:
第一,由产业结构单一化衍生的多重问题
1977年底,闵行卫星城总面积约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9万人,其中在职职工共6万余人。卫星城内有市属企业29家,职工4.8万人。这与原先的规划指标相距甚远。到1979年底,闵行卫星城的常住人口规模下滑至7.2万人,其中在职职工5.8万人。在卫星城所有的50家工厂之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为33家,职工5.5万人。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有将近1.8万人迁出了闵行卫星城。但从常住人口降低的数值高于在职职工减少的数值这一情况分析,应当是非产业劳动人口迁出较多。
至于个中缘由,产业结构单一化是主因。闵行卫星城是以重型机电工业为主,在卫星城建设过程中,过于强调提升主业的地位,而忽视了多元化配套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人口比例失衡问题。在闵行卫星城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中,女工占比仅为30%,这虽然符合重工业的生产操作要求,但男性职工占比过高,也容易产生婚恋难等诸多社会问题。当时,要在远离市区的闵行地区谈婚论嫁,多数仍然依靠地缘、业缘关系解决。因此,不少青年男工在闵行找不到对象,影响他们在当地安心工作和定居。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产业结构的过度单一化也形成了就业排他性,使闵行卫星城的就业人口高度集中于相关企业中,而与重型机电工业无关的劳动力逐步被淘汰,闵行卫星城常住人口数量下降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重生产、轻生活”,生活设施配套发展滞后
较之现代化工业生产,闵行卫星城的生活设施配套发展则显滞后,这主要体现职工住房问题上。从1960年代初到1974年,闵行卫星城的住宅建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974年至1978年6月,闵行虽建造住宅8.7万平方米,但远不能满足数以万计的职工居住需求。1978年,闵行卫星城有2.9万余名职工家住市区,占比达47.5%,其中有1800户期望迁居闵行,但无房可供;在剩下的约3.1万余名住在闵行的职工中,有2000多困难户,还有600户职工因无住房,只能以高价租赁农民的房子。因此,闵行卫星城职工带眷比例仅为38%。从见,闵行卫星城非但未能发挥人口和产业互动、职住互动的作用,相反还出现了人户分离、职住分离等问题,卫星城的“反磁力中心”功能弱化。
商业配套设施曾是闵行卫星城规划建设中的一大优势,尤其是“闵行一条街”一度成为国内人居环境建设的典范。可是,闵行卫星城的商业服务网点并没有伴随人口的增长而得到相应发展。至1970年代末,商业配套设施缺失的问题引起了居民的普遍不满。以昆阳新村为例,当地仅有一个临时商品供应点,居民想吃一碗阳春面还要花3角钱车费,跑去别地。
上下班交通问题也同样困扰着闵行卫星城的发展。由于闵行通往市区徐家汇仅有徐闵线一条公交线路,班次少,运营时间短,大部分企业只能自行运营通勤车辆,接送职工上下班,开支较大。上海电机厂1979年全年通勤车投放为4752车次,营运维护费用达41万元。这无形之中增加了企业负担。
第三,城乡二元体制成为吸引人口聚集的体制机制障碍
在闵行卫星城建设发展初期,实施了一些优惠政策,的确吸引不少职工迁居闵行,如在住房分配和房租标准上都略优于市区,商品种类和文化业余生活内容都基本与市区一致,个别方面还有优先供应。但到了1970年代,城乡二元体制在闵行卫星城被重新强化,原先的优惠政策都被逐步取消:住房分配和房租标准与市区看齐;商品供应基本参照郊区标准;整个卫星城只有剧院、书场、体育场各一座,原有的工人俱乐部和少年宫均被改作中学,群众业余生活单调枯燥。许多职工因此不愿在闵行卫星城定居。
由于闵行卫星城是依靠国家投资、以产业为先导而建设起来的工业化卫星城,在“大跃进”时期展开的一期规划的先期落实情况相当理想,各项预定目标均按时甚至提前完成。但因受到三年困难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的影响,上海基本建设投资额大幅度压缩,接踵而至的“四清”、“文革”运动,又严重扰乱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上海的工业建设出现停顿乃至倒退,这些极大阻碍闵行卫星城一期规划后续项目的实施,使规划与现实之间出现严重偏离。
在1958年编制规划、1959年修订规划之后的20年间,闵行卫星城未出台新的规划方案,其发展建设处于失速和无序状态。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的禁锢和城乡二元社会固化等的制约,卫星城难以发挥产业密集的优势,人口聚集的“反磁力”效应也大打折扣。
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恢复闵行区建制,闵行、吴泾两个卫星城同时纳入闵行区境。为协调发展,闵行区人民政府编制了《闵行区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此后,闵行卫星城规划一再调整,发展从此驶入快车道。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卫星城建设规划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从必然性来说,是执行“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的要求;从偶然性来看,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打乱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正常实施,也迫使上海原有的工业建设计划提速落实。可以说,历史的必然性催生了上海卫星城规划的出现,历史的偶然性又大幅度加快了这一时期上海卫星城从规划蓝图到付诸实施的步伐。
通过对闵行卫星城建设初期发展情况的梳理不难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卫星城规划的空间布局是比较合理的,因地制宜、分步推进的建设方式也行之有效。卫星城的产业布局依据“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较为符合当时上海经济发展实际。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各个卫星城过于强调主业发展,忽视了主辅产业的多元化协调发展。
毋庸置疑,由于政治环境的剧烈震荡和经济政策的急速转向导致上海卫星城规划建设出现断层,进而发展停滞,使原有规划中的弊端被一再放大,累积形成矛盾。闵行卫星城在1970年末所遭遇的各类问题即是一个缩影。
闵行卫星城的规划建设历史告诉我们:郊区新城的规划须有连续性,建设必须坚持长期性。任何规划都难免带有局限性,要依据母城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方针的变动而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建设也同样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根据规划及实际发展情况,分期实施,循序渐进。
人口疏散是郊区新城的主要功能之一,新城应在人居环境建设与治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基础设施优化等方面达到甚至超越母城的水准,朝着宜居城市的方向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具备较高能级的城市综合集聚辐射功能,真正实现产城融合。
(作者系上海市档案馆馆员,《上海档案史料研究》责任编辑。本文系作者向上海大学历史系主办的 “城镇化道路与上海卫星城”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发表时有改写。)
